2014年第11期《新西部》雜志獨(dú)家策劃��、特別報(bào)道

策劃/本刊采編部 撰文/楊旭民
1994年12月8日����,新疆克拉瑪依的一場大火,導(dǎo)致325人遇難�����,其中包括288名中小學(xué)生,數(shù)百個(gè)家庭的命運(yùn)從此被改寫���。
20年之后�����,那場大火留給這座城市的痛苦烙印���,依然隨處可見?����!澳羌聝骸?�、“那個(gè)日子”����,是克拉瑪依人對那場災(zāi)難的稱呼;而那些死傷者��,則被統(tǒng)一稱作“12·8”人���。
克拉瑪依大火發(fā)生后��,央視“焦點(diǎn)訪談”派記者陳耀文進(jìn)行了深入細(xì)致的采訪�����,但是����,由于當(dāng)時(shí)當(dāng)?shù)厝罕娗榫w極不穩(wěn)定���,央視領(lǐng)導(dǎo)壓下了這期節(jié)目�����。陳耀文得知節(jié)目無法播出�,這位西北漢子曾哭得抬不起頭����。12年后,他以另一種方式將大火內(nèi)幕公之于世�����。
克拉瑪依大火發(fā)生20年�����,無論是媒體還是公眾,對這場災(zāi)難的關(guān)注和追問都是持久而又固執(zhí)的���。2006年�����,《南方周末》頭版推出紀(jì)念專稿《克拉瑪依大火:一個(gè)輪回背后的真相》�����,其中包含了對那句著名的“讓領(lǐng)導(dǎo)先走”的再次考證��。
2008年�,一個(gè)叫徐辛的攝影人歷時(shí)半年時(shí)間���,從克拉瑪依到烏魯木齊��,再到北京�、上海等地����,尋找大火遇難者家屬����。他從60多位受訪家長中�����,截取13個(gè)遇難孩子家庭為樣本�,剪輯出一部時(shí)長達(dá)6小時(shí)的紀(jì)錄片—《克拉瑪依》��。他說��,“如果不是希望這個(gè)國家更好��,我根本沒有必要去拍這樣的東西���?��!?/p>
這場大火,實(shí)在包含了太多的痛����,太多的淚,太多值得反思的東西。
紀(jì)念災(zāi)難���,就是為了避免更多災(zāi)難的發(fā)生��。
正因此����,我們才再次走進(jìn)了克拉瑪依……
【請點(diǎn)擊這里閱讀詳細(xì)內(nèi)容】
克拉瑪依一個(gè)隱秘的傷疤 文/本刊記者 李 嵱

在克拉瑪依��,雖然那場大火已過去20年�,但痛苦的烙印依舊可見。
廣場上的友誼館��,像一塊紀(jì)念碑獨(dú)自兀立�����;更多的傷痛��,深藏在親歷者背井離
鄉(xiāng)的身影里��,抑或是遙遠(yuǎn)的記憶深處�����。
幾百個(gè)墓碑上,在同樣的位置����,鐫刻著一個(gè)同樣的時(shí)間—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。隨著時(shí)間的流逝����,很多年輕的人們已無從了解隱藏在這串?dāng)?shù)字背后的那段往事?����!?a >詳細(xì)??????】
一盤未播放能的節(jié)目帶文/本刊記者 秦 灃

時(shí)間是上天為每一段傷痛開出的最好藥方�����,但時(shí)間恰恰也是檢驗(yàn)我們心靈是否健全的那根標(biāo)桿�����。
悲痛可以因?yàn)闀r(shí)間的延走而趨于麻木��,而罪責(zé)卻不會(huì)因?yàn)闀r(shí)光的隱匿而消失����。“向前看”的理論���,也不能拒絕我們作為人類對自己過失���、錯(cuò)誤以及罪孽的救贖。
【詳細(xì)······】
大火幸存者口述實(shí)錄采訪整理/李 嵱 陳小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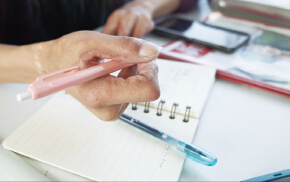
我是生還者中年紀(jì)最小的女孩—到處是尖叫和哭聲—地是冰涼的�����,然后我感覺有風(fēng)了—你們明白缺失者的痛苦嗎����?—難道我連一份愛情都不能擁有嗎?
你要漂亮還是要活著����?要活著!
周圍人對我們這個(gè)群體有一個(gè)特別的稱呼:“12·8”人���?�!?a >詳細(xì)······】
在沒有坐標(biāo)的戈壁上遠(yuǎn)行 一位父親的漂泊和懷念文/圖 本刊記者 丁 蓉

“懷念有時(shí)會(huì)令人傷逝和感悟���,但懷念更會(huì)使靈魂慰籍和凈化����?����!?/p>
他雖然接受了記者的采訪���,卻不想讓讀者知道他的名字�。20年前�,這位父親失去了女兒,從此�����,活著對他來說成了一種懲罰�����。
然而�����,生活自有一股推著他向前的力量����。“順利與不順利的路���,不妨都抽象地走走���,且要結(jié)合實(shí)際地想想,關(guān)鍵是要能回得來���,回到現(xiàn)實(shí)中來�,這樣你就會(huì)有選擇地知道應(yīng)該怎樣繼續(xù)生活下去�。”他說����。【詳細(xì)······】
徐辛與他的《克拉瑪依》文/本刊記者 陳小瑋

徐辛在《克拉瑪依》拍攝之前�����,對克拉瑪依大火的認(rèn)識(shí)就是“一個(gè)火災(zāi)”�;剛拍完,他覺得政府處理方式非常愚蠢�,深思后認(rèn)為����,這場大火導(dǎo)致的悲劇���,把中國的弊病全部展現(xiàn)了出來�����。
“如果不是希望這個(gè)國家更好��,我根本沒有必要去拍這樣的東西�����?��!彼f?��!?a >詳細(xì)······】
(責(zé)任編輯 王順利)

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(wǎng)
掃一掃上新西部網(wǎng)
 不良信息舉報(bào)窗口
不良信息舉報(bào)窗口



